即使把岁月冲刷成一道漫长的河流,鱼也一定能溯着流波游回到生命的源头。
我又该依靠什么找到回乡的路,回到爹娘和兄长守望着的老家?
当我坐在书桌前闭目遐思的时候,街上零星响起的鞭炮声一下子唤醒了我的灵感——就用我这流浪狗的鼻子吧,我想,只要嗅着那股熟悉的年味儿,我就一定能找到故乡,找到被岁月尘封已久的童年。
哦,我的故乡,我的童年。

01、故乡的年味儿,带着声响
故乡的年味儿,最早是从满街筒子乱跑的孩子那里散发出来,那是爆竹炸裂锦帛般四散的欢乐。弯弯曲曲的土街,低矮而粗陋的石头墙,墙根里还散放着玉米秸、棉花柴之类的柴垛,而满大街奔跑着的全是穿着粗布棉袄棉裤的像我一样大的野小子,时而会从口袋里掏出大大小小的爆竹,继而就会传出声声脆响:那清爽而干脆的是小红鞭,那浑厚得让人们捂上耳朵的是“大雷子”,那一前一后先低后高响彻云霄的是“二踢脚”……我们围在一起一边显摆着口袋里的鞭炮,一边商量着坏主意:那个拾粪看坡成天吓唬人的董老头过来了,我们把鞭炮塞在墙角石头缝里,看他走近了,我们点着,躲藏好,董老头刚走到街角,“砰!”鞭炮炸响,董老头浑身一哆噎,粪筐几乎掉了地上。他站在那里,四处搜寻着我们,嘴里骂着脏话,我们拍着手,跳着跑着气他……
我们比赛着把点燃了的鞭炮扔在水塘里,看谁的能够炸起水花;我们把鞭炮依次插在提前打好了小孔的冰面上,然后喊个“一二!”分别点燃,看那三四个大雷子能否炸开厚厚的冰;我们把鞭炮插进雪团里,偷偷地放到女孩子戏耍着的队伍里,然后看炸起的雪沫溅她们一身,听她们无奈地骂人,谁怕她们?除了骂,最多也就向大人告个状,到年了,反正大人也不会揍人!
当满街筒子奔跑着野小子,当那黄土混着炸药爆碎了纸屑的鞭炮声响起,当孩子们的快乐被那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迸溅成树树梅花的时候,所有的人便都知道年要来了。
02、故乡的年味儿,颜色金黄
我不知道朋友你小的时候是不是特馋,反正我们那代人特别馋!也许是因为七零年左右出生的孩子童年太穷,一年到头几乎吃不到油水,除非过年或者有亲戚串门的时候才能见到肉的模样,即使吃不到嘴里,伸长脖子使劲闻一闻肉味似乎也能饱三天,而跟着大人赶年集是我们小时候最盼望的美事儿。
每年的腊月二十五,是我们附近几个村必赶的一个大年集,我们提前好几天就缠着大人,到了那天,早饭也不好好吃,直到大人答应了,动身了,我们就屁颠屁颠地跟在大人后面去赶集,走出村子,通往集的小路上,赶集的人已经扯成一条线,几乎还没看到集的影儿,就远远地听到集上卖鞭炮的摊子比赛自己的鞭炮声,我高兴得像撒欢的小毛驴,一溜烟地跑到大人前面老远,耳朵里传来各种各样的吆喝声,我似乎看到了吹糖人的小货郎熬得发亮的糖稀,看到他们用麦秸杆吹好的小猪小牛小毛驴,我似乎听到了卖胡辣汤的扯长了嗓子像唱歌一样的叫卖声,我似乎看到了那个平时算命的王半瞎子用红线条围成场子,他一准在那场子中间打着老大的竹板儿说着评书《杨家将》,看到他的小徒弟拿着个搪瓷茶缸转着圈儿敛钱的样子……
当然,这些都很有吸引力。但真正有吸引力的是在跟着大人买好了年货之后,不管人群多挤,平时一分钱也不舍得多花的爷爷也一定会把我领到煎包铺,眼睁睁地等着人们空出个座,赶紧坐在那里,然后看爷爷站在煎包的平锅前,给我叫上四五个大大的煎包儿,每一个煎包儿都被明晃晃的油煎出金飒飒的翅儿,咬一口,那包子里就会漾出满嘴的油,爷爷坐在那儿抽他的老旱烟,微笑地看他的馋嘴儿孙子饿虎一样的吃包子,有时我也奇怪,爷爷根本就没吃,为什么看他望着我的样子,似乎比吃包子都感到满足和快乐……
那时,我不懂。
当我开始懂的时候,他已离去。
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的,还有童年,我再也不是小孩子……

03、故乡的年味儿,是一件新衣裳
也许大部分60后、70后的童年都没穿过几件新衣裳,尤其是家里排行老二的我,身上穿的几乎都是哥哥穿剩下的缝缝补补的旧衣裳。为此我没少和娘闹气,甚至有时怀疑自己真是路上拣来的孩子。
“过新年,穿新衣。”这是我串起我整个少年时代的新年愿望。
当然也不光我,家家户户的孩子似乎都这样,东邻西舍的男孩女孩差不多一样。
当爹娘的肯定知道。他们老早就给儿女们准备好了新衣裳,但他们平日里一句话也不提,更是把新衣裳藏在柜子里。有时看着小伙伴们都穿上新衣裳到处显摆了,我和哥哥有时会急得咧嘴哭。娘倒不急不恼嘲笑我们哭的样子特别丑。
直到大年三十早晨,我们醒来时,娘早在我们枕头上摆好了新衣裳。
我和哥哥穿上新衣裳激动得脸也不洗饭都不吃就跑到大街上,找自己的小伙伴炫耀。
一件新衣裳,让儿时的新年有了幸福的记忆。
04、故乡的年味儿,是油汪汪的四只猪蹄
每年的腊月二十七,家家都会飘出煮肉的香味,我们这些疯在街上的野小子,也一趟一趟地往家跑,进了家直奔厨房,使劲抽着鼻子,好把那锅里飘出的煮肉的香气更深地吸进肚子里,然后一遍遍地问烧火的娘:“熟了吗?快熟了吗?”娘一边往灶膛里填柴,一边逗笑:“你再来问第三遍的时候,就快熟了。”于是,我就一趟趟地跑出去,又像把什么丢了家里似的跑回家,好像那锅里的肉煮不熟就没有心思玩了似的。
说起印象最深的过年,我和哥哥同时提到了兄弟俩啃四只热猪蹄那事。
那是香了我整个少年时代的记忆,那是我印象当中最难忘的一年。
那年,娘喂了一整年的大肥猪杀掉后,一整套软硬下货(有的地方可能叫下水)全留了下来,光那猪头、猪尾巴还有猪蹄子外加几块剔下来的大骨头就煮了满满一锅!
煮好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和哥哥上午饭也没认真吃,因为娘说晚上煮肉空空肚子也可,爹和娘用一个面盆盛着四个猪蹄放在我们面前:“你们兄弟俩愿意啃就啃光吧,要啃干净,别败坏。”
我和哥的眼睛里登时放出了明亮的光,那四只猪蹄子真胖,几乎占了半盆子!我们伸手就抓,然后不约而同地放了下来——太烫了,刚捞出来就给我们端来了。我们一边甩着手,一边找筷子夹起来,那煮得金黄色的猪蹄不一会儿就被我们啃得乱七八糟,爹过来拿起我们啃得不像样子的猪蹄,帮我们拆开,然后教我们吃那蹄甲儿,筋那么地韧,皮那么地脆,把蹄甲拆开后啃起来竟然能啃得那么光溜溜……
虽然馋得不像样,但那年,我和哥的肚子竟然就没能装得下四只猪蹄儿……
真应了那句老话,过年每天都是好日子。
当家家洗萝卜剁馅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今晚到了过年炸丸子的时候了。
相比较煮肉,炸丸子的诱惑就小了许多,但即使如此,第一锅丸子在给老天爷上供之后,娘会端着碗招呼我们兄弟吃——小的时候,好像我和哥哥都特别馋,妹妹倒显得“有材料”,显得很文雅的样子。
热丸子我们倒吃不了多少,也许这几天接连吃好东西的缘故吧,但炸好的丸子不论娘藏得多严实,不论挂得多高,我和哥哥总能想出法子偷着吃,因为偷吃丸子,我们争过闹过也相互给爹娘告过状,但更多的时候是合作,一个放哨,一个作案,然后把偷出来的丸子平均分开。
有时,娘会发现丸子少得太快了,吃饭的时候她就会问我们,我们一个一个把头摇得像转铃,满脸还挂着委屈的样子,娘没法子,会把筐子摘下来,给妹妹专门拿几个弥补一下。我们就低了头吃饭,装做不想吃的样子,有时就忍不住笑,甚至会笑得坐不住了,吃不下饭了,被娘一阵子笤帚疙瘩揍了出去。
每年最多过了初十,或者十二,似乎家里也没正经地吃过几次丸子,那挂在梁头的一满筐丸子就被我们吃光了,最后连那铺筐子底的煎饼都会被我们抢得干干净净!
当丸子也已经被我们偷光了的时候,年算真正地走远了,走得没有了痕迹。

05、故乡的年味,游子最难忘记
故乡难回。日子走得越远便越难回,更多只能在梦里,就像品那儿时的年,一次次品,品得口齿生香,品得两腮泪垂。
最远莫过回乡路,最痛莫过思乡诗。
长大后,我离开了家,爹娘住着的那几间老屋成为故乡。
二三十年的日子流逝在时间的河里,找不到任何踪迹。也不能说找不到踪迹,那个傻傻地疯玩的野小子已两鬓斑白,当年爷爷眼中的馋嘴孙子已经到了当爷爷的年纪!
当年,我们胆战心惊地偷吃丸子的情景依然在眼前,当年摸着黑用煎饼偷偷从熟肉盆里卷肥肉结果卷起的却是大块姜的镜头似乎就在昨天——那凉透了的油炸丸子是那么那么香,那条被我和哥哥踩着偷丸子的椅子和板凳早已不知去了何方!
现在的孩子,早已没有偷吃丸子的兴趣,别说白白的肥肉片子,就算精心配制的鱼和肉推到他们眼前,也很难引起他们的胃口,那么,他们还会像我们小时候那样渴望过年吗?在他们的心中,年的味道又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于我而言,年味就是克服各种不习惯回到老家,围着熊熊的煤炭炉子,一边包着饺子,一边听家人拉扯似乎永远扯不完的陈年往事。
叫着儿子,给所有的门院贴上红红的春联;学着爹的样子,坐在沙发上捏着金黄的元宝,然后领着儿子,手拈一根香,向爹娘一生信奉着的天爷爷、灶爷爷、财神爷爷和保家姑跪拜,祈祷,求福。
壹点号 壹粉唐长老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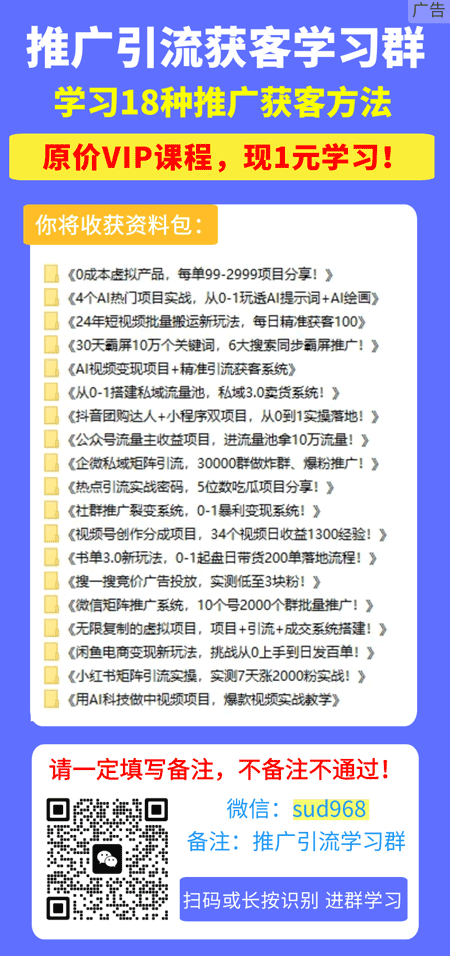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sumdns.com/16534.html
